從8月份《關于開展城鄉居民大病保險的指導意見》初次亮相以來,號稱“城市反哺農村”的大病醫保便備受社會各界關注。其籌資是從城鎮居民醫保基金、新農合基金中劃出一定比例或額度,但據有關人士估計,三年之內,全國新農合的統籌基金就將用完,屆時,大病醫保將如何度過三年之癢?
據悉,大病醫保的實施細則將在國慶后出臺,業內人士預計,具體的籌資辦法應該基本劃定在《指導意見》顯示的途徑內,即基金有結余的地區利用結余籌集大病保險資金;結余不足或沒有結余的地區,在城鎮居民醫保和新農合年度籌資時解決資金來源,逐步完善籌資機制。
雖然新農合資金一向結余較多,但據測算,如果大病醫保的籌資水平為40元/人,那么全國新農合的統籌基金三年就將用完。
城鎮職工醫保的情況也不見得樂觀。雖然其制度設計中預先就搭載了大病醫保的有關條款,此次暫時不需要額外支出,但在人社部否認了醫保基金個人繳納比例提高傳聞的情況下,背負著報銷目錄擴容、大病醫保籌資等重壓的醫保基金,將不得不另辟蹊徑應對支付困境。
確切消息稱,2011年上海和北京的城鎮職工醫保基金都已出現收不抵支。中國社科院一項有關測算得出初步結論稱,城鎮職工醫保將在2017年出現普遍赤字,也就是二線以上城市的城鎮職工醫保基金將無法做到當年平衡。
顯然,隨著醫保基金支出壓力增大,醫療費用控制就尤為迫切。自2011年下半年開始,本輪新醫改日益把醫療費用控制擺上顯要位置,支付方式改革的重要性也日益迫切。然而總額預付的先天不足,既無法管控到目錄外支出和自費病人的花銷,另一方面,按病種付費卻因其數據要求高、測算復雜,試點工作進展緩慢。
控制醫療費用,無論對于醫療機構,還是對于醫保基金,都成為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
國務院醫改辦曾針對居民醫保和新農合抽取1億人樣本調研,測算出大病發生概率為0.2%-0.4%,即三四百萬人口規模的地級市,醫療費用超過20萬元的個案一年不超過5例。由此測算下來,平均每人每年從醫保基金拿出40元,即可保障大病。
據統計,新農合和城鎮居民醫保的基金累計結余1300多億元,可以應付未來三年的籌資需求。
但是,三年后的資金來源不得而知。雖然財政每年都在增加對居民醫
保和新農合的補貼,但醫療費用也平均每年以15%的速度增加。基本醫保基金的當年結余率近幾年來又一直在有意降低,僅僅依靠累計結余并不足為長遠之計。
城鎮職工醫保的狀況也不容樂觀。《2011年度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披露,截至2011年末,城鎮基本醫療統籌基金累計結存4015億元(含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基金累計結存497億元),個人賬戶積累2165億元。
看似充足的數字背后暗藏隱憂。隨著“擴面”工作的基本完成,基金的增量部分越來越少;人社部此次辟謠了籌資比例提高的傳聞,也進一步證實未來城鎮職工醫保的總盤子基本固定。
然而基金的支出卻會不斷增長。一方面是隨醫療費用“水漲船高”,另一方面城鎮職工醫保一直是“單基數繳費”,也就是在職人員繳納而退休人員不繳。
醫保改革全國試點、江蘇鎮江人社局醫保處王翔透露,當地的供養比(退休人員相對于在職人員的比例)已超過2.1,江蘇全省的平均數更高達3.17。
另外不容忽視的是,從機關事業單位退休的參保人員,其繳費基數遠高于企業人員,以鎮江為例,前者僅為1617元/月,后者達5000元/月。當從統籌基金中劃撥同樣的比例以形成個人賬戶時,前者對統籌基金的占用遠遠超過后者。
有統計顯示,退休人員的平均醫保基金花費是在職人員的三倍。多位實操及理論界人士擔心,在人口老齡化比較嚴重以及青壯年人口大量流出的地區,城鎮職工醫保基金將難以承受。
人社部的政策研究專家表示,如果依據上述估算,把退休人員的籌資標準提高為在職人員的3倍,這顯然不現實,而如果提高得少則所起作用有限,因此“單基數繳費”的現狀暫時看不到改變。
醫保基金的捉襟見肘,首先從優質醫療資源豐富,以及基金管理水平高因而結余較少的地區體現出來。
上海有關醫保專家曾透露,上海城鎮職工醫保基金的統籌部分已經透支,目前靠挪用個人賬戶資金在支撐。不過上海官方對此予以否認。
鎮江作為全國最早建立城鎮職工醫保的城市,較長的積累期曾留下較多基金結余,但在多種支付壓力下,去年統籌部分已出現當年虧損,開始“吃老本”。
另據了解,江蘇省多個地方的城鎮居民醫保也已連續幾年超支,在用歷年結余甚至風險基金支撐。
在支付壓力日益增加的時候,上海城鎮職工醫保獲得了一筆“雪中送炭”的資金注入:上海市外來人員綜合保險中的有關部分。
上海市規定,在本地務工或經商,但不具有本地常住戶籍的外地人員,都應當參加綜合保險。綜合保險包括工傷保險、住院醫療和老年補助三項待遇。上海市社科院研究員胡蘇云向記者透露,上海新近決定把這筆資金交由上海人社局統一管理,其中住院醫療和老年補助的資金,分別注入人社局管理的城鎮職工醫保賬戶和養老賬戶。
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外來人口與上海戶籍人口比已達2:3,因此雖然外來人員綜合保險的籌資水平很低,但資金總額相當可觀。
尤其是考慮到17-43歲年齡段的青壯年人口中,每歲組都是外來人口比上海戶籍人口多,而現在無論是醫保基金還是養老金,跨省的轉移接續實際上都還不可能實現,當這批人返鄉時,他們所繳納的統籌基金就被留在了上海,客觀上補貼了當地人口。
胡蘇云告訴記者,由于綜合保險資金的注入,上海的社保基金已從最近幾年的當年收不抵支一躍扭虧為盈。
在此次全國開展大病醫保中被奉為藍本的太倉模式,也存在著外地勞動人口對當地戶籍人口的補貼。
太倉醫保基金結算中心的數據顯示,當地城鎮職工醫保的參保人數為40多萬,其中公務員和國有事業單位職工參保人員共約3萬人,而太倉國有企業很少,且有一部分垂直系統管理的企業不在當地參保,城鎮職工醫保的參保主體是民營企業職工。
另有數據顯示,太倉外來人口47.7萬人,其中青壯年約占90%。綜合以上數據不難推斷,外來勞動力人口是當地城鎮職工醫保的一大參保主體,他們對本地參保者存在著事實上的補貼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太倉新農合已與城鎮居民醫保并軌且統一由人社部門管理,這種制度上的高度一體化,成就了當地大病補充醫保中“城市反哺農村”的制度設計。
具體而言,太倉大病補充醫保實行差異化繳費和公平化待遇,城鎮職工繳費占總保費的比例為83%,居民繳費占17%。但職工群體所獲補償金額為總金額的48%,居民為52%,居民實際報銷比例的提高也高于職工群體。
太倉人社局局長陸俊指出,上述過程實際上也是一種“二次分配”。毋庸諱言,在這種對弱勢群體和農村人口的傾斜中,外來人口作了不小的貢獻。
對此,太倉醫保結算中心主任錢瑛琦認為,外來人口繳費年限少,且繳費基數往往偏低,但參保后的基本醫保、特別是大病醫保待遇與戶籍人口相同,因此他們也享受到了制度的好處,不能完全說是對他們不公平。
誠如錢瑛琦所言,外來人口的所謂“反哺”在發達的人口流入地區普遍存在。但從長遠來看,社保的統籌層次將不斷提高,跨統籌區乃至跨省的轉移接續工作也將不斷推進,城鎮職工醫保的支付壓力,還需要尋找更為可持續的解決之道。
消息人士透露,日前保監會召集了8家保險公司進行討論,包括國壽、平安、太保、人保、陽光等。“但最終批復參與大病醫保資格可能要到年底。”
而大病醫保的推出,團體險業務無疑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團體險是指保險公司以一份保險合同為已存在的某團體內多位成員承擔保險責任的業務。在我國恢復保險業務之初,曾是保險業的主要業務組成部分。發展至今,主要險種包括團體醫療健康保險、團體意外保險以及少量的團體壽險產品。但隨著個人保險業務的興起,在保險公司中的地位開始降低。
“目前全行業整體團體險保費規模在300億元左右。大病醫保新政并沒有對保費繳納標準有統一規定,而是由各地根據情況具體設定。假設按照每人50元的保費收入計,全國13億人民保費收入將達到650億元。”某壽險公司團體險負責人如此預測,由于明年是第一年施行,各地推動速度可能不一樣,所以保守估計,明年或有200億元的保費收入入賬。
這位負責人表示,在人員配備等方面,保險公司現有的團體險隊伍基本夠用,不需要增加太多投入。
實際上,多家保險公司在承辦大病醫保方面已有不少經驗。除了人保健康險的湛江模式、太保壽險的江陰模式等常見諸報端的范例外,陽光保險相關負責人也向《中國經營報》記者介紹了陽光與襄陽市政府合作的“襄陽模式”:由襄陽當地醫保基金籌資每人20元,城鎮居民患病支付合理費用超過3萬元,超出部分將由陽光保險按一定的比例支付,公司支付封頂為9萬元。
除大病醫保外,稅延型養老保險若能推出,也或將為團體險帶來機會。“個人稅延型養老保險應該由團險渠道來做,但它嚴格意義上說不是團體險,實質上是個人保險,所以也可能會成立獨立團隊。”上述壽險公司團體險負責人表示。
“波士頓咨詢公司曾預測中國團體險市場規模會很快突破千億元。”美國大都會集團執行副總裁和全球員工福利業務負責人Maria R Morris稱,毫無疑問中國是一個巨大的團體險市場,因為目前中國中小企業達1100多萬戶,占全國實有企業總數的99%以上。也因此,中美聯泰大都會將客戶定位在中小企業。
但有了險企助陣,并不意味著大病醫保可以順利度過三年之癢。新農合基金如何順利運作、未來是否能夠滿足農村龐大的醫保要求,還是一個未知數。但無論怎樣,大病醫保的出臺還是讓人看到行業的一絲曙光,我們也期待大病醫保能夠走得更遠、更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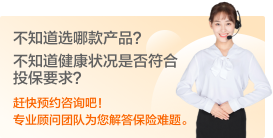

您的信息僅供預約咨詢所用,不泄露至
任何第三方或用于其他用途。


![]()
正品保險
國家金融監督快捷投保
全方位一鍵對比省心服務
電子保單快捷變更安全可靠
7x24小時客服不間斷品牌實力
12年 1000萬用戶選擇